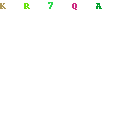
老屋,你在我梦里
张守梅
五岁那年,爹因病去世,娘带我们姊妹四个回到了姥姥。在这里,我们有了另一个家,也是我居住过十年的老屋。老屋坐落在村子的低洼处。院落很大,房子却不多,和所有农村房子一样,坐北朝南,一溜五间草房,只在屋檐处压了两趟青瓦,西边两间低矮的草房算作伙房。叔在家中排行老四,其他的兄弟都成家分开单过了,叔因为兄弟姊妹多,没有结婚,就和父母住在一起。娘领着我们一帮孩子去了以后,叔也算成家了,虽然也是分开单过,但那时叔的父母年事已高,没能力再置办一处房子,于是我们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了一个院子里。
过去都讲究东边方向是尊长位,就按规矩把东头的两间分给了爷爷奶奶,在外面的一间贴北墙支了锅灶,贴北墙摆放一张四方的八仙桌,八仙桌前面是一张长方形的木头桌子,作为吃饭和待客用。里间盘了一铺炕,一年四季爷爷奶奶都睡在炕上,冬天一烧火做饭炕就很暖和,夏天就不敢用大锅烧火做饭了,只能在院墙根儿,用三块石头支一个“野锅子”烧火做饭。
我们一家六口住在了西头的三间屋子里,只有一个门。我和姐姐住在东里间,南北方向放着一张大木床,是从我们原来的家带过来的,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,从我记事起它就是黑色的,泛着岁月粗陋的幽光。床北头摆放着娘给的木箱子,用一张自制的木凳支着,与床持平。晚上写作业的时候,我把煤油灯端过来放在木箱顶上,这时木箱就成为了书桌,床就是我的凳子。
姐姐从外面借来好书了,我匆匆地写完作业,和姐姐头对着头,就着昏暗的油灯津津有味地看着,不知不觉时间就晚了。娘在西屋喊:“都啥时候了还点灯熬油的?”我赶紧把书藏起来,回答娘:“还没写完作业呢,快了,写完了就吹灯!”然后我和姐姐就“吃吃”地笑,再偷偷地看一会儿。冷了,也困了,我们就赶紧缩进被窝里。我和姐姐通腿儿睡,冬天她就愿意贴着我,说我像个小火炉子一样热乎;夏天就让我离她越远越好!
其实木箱子里也没什么好装的,也就是夏天装几件棉衣,冬天装几件小褂,平常穿的衣服都搭在床北边的“搭杆子”上。所谓的“搭杆子”,是一根较光滑的、大拇指粗细的竹竿,两头拴根绳子,挂在墙两边的钉子上,无论是换洗的衣服,还是晚上睡觉时脱下的衣服,随手就搭上去了,节省很多的空间。若是下雨天,外面有未晒干的衣服,就把干衣服堆在一头,湿衣服也晾在“搭杆子”上。
老屋是木制的门窗,两扇木门一关,整间屋子都是黑暗的,只在闸板底下微微透一点儿光。夏天把冬天糊上的窗户纸撕掉,经过了一个冬天的风吹雪侵,白色的窗户纸已泛黄。后来有了塑料薄膜就好多了,天冷了,就去供销社割几块塑料薄膜,买一把鞋钉儿,找几根秫秸杆儿从中间剖开,将薄膜按照窗户尺寸裁好,姐姐用手摁住,二哥把秫秸杆儿对准窗户的四个边角,拿鞋钉儿钉上一圈儿,再也不用担心冬天呼啸的北风吹破窗户纸灌进屋里。
老屋的北墙没留窗户,那年夏天特别热。不通风的屋里像蒸笼一样,任蒲扇怎么摇也无法驱走滚滚热浪。实在没法子了,叔就在三十多公分厚的土墙上,硬是抠出了一个小窗户。我家屋后是一条窄窄浅浅的小河,只在雨季才会有淙淙的流水。那个夏天的雨水特别充沛,每当雨后,会有清凉的风从窗户吹进来,带着小河里水草的气息,那些夜晚,梦格外甜。
睡觉的屋子同时也是库房,农村的房子窄巴,需充分利用一切空间。有一年土豆大丰收,哥推回来一大车土豆,土豆见光容易发绿,所以不能放在外面,实在没地儿放了,就堆在了我和姐姐的床底下。整个冬天,床底下的老鼠窜登得特别欢,每晚都能听见这些小东西“吱吱吱吱”的叫声……那一大堆土豆,整个冬天也没吃完。第二年春天,娘准备拾掇出来馇猪食,我钻进床底下往外巴拉,却看到土豆芽都长得顶到我们的床板了。不光是土豆芽,还有屋后紧靠房檐的大槐树的根,也历尽曲折钻到床底下来,还顽强地长出了几棵小树,未见阳光的嫩黄小芽,已经被床板压弯了!
老屋中间的堂屋,正中摆一张枣红色的带三个抽屉的桌子,桌子前面是一张饭桌,听娘说是砍了我家一棵大楝树找木匠做的,虽不是很光滑,但很耐用,娘直到现在还用着呢。正中墙上贴着中堂画,东南角门后头放着一个大缸,缸上面摞着个一搂搂不过来的大瓦盆,里面装满了娘用地瓜面烙的煎饼,叠得板板正正,一摞摞摆在大瓦盆里。装在瓦盆里的煎饼既保湿又防潮,吃很长时间都不会坏。每天一放学,我和二哥回到家就直奔煎饼盆,掀开上面的盖顶掏出煎饼,从酱缸里撅一筷子娘自己做的豆瓣酱卷上,咬一口,那个香啊!
饭桌西侧靠墙根儿支了一个碓臼,每天早上,我们还没起床呢,娘就开始掐(音译)碓了,或花生米,或榨干油的花生饼,“嘎登,嘎登……”,姐姐先起床了,娘就让姐姐掐碓,她去拾掇锅,等我们都起来后,饭也就做好了。有时是放了掐碎的花生米、萝卜菜,再搅上玉米面做的咸饭;有时是放上掐碎的花生饼、萝卜菜熬的咸地瓜,无论怎么换花样儿,都是很难见到肉的。
出堂屋门口,在西墙根支着一盘石磨,村里还没有粉碎机的那些年,所有需要磨碎的粮食都靠这盘石磨。碓臼和石磨,是那个年代庄户人家的标配,但也有日子过得更寒酸,支不起一盘磨的,那就只能抽谁家有空闲,就去借谁家的磨用。
西边还有两间草房,屋檐处连两趟瓦都没压,是做厨房用的,里面支着一口做饭用的大锅,还支了一盘炕,大哥和二哥睡在炕上。叔和娘每天早早起床,娘做饭,叔坐在旁边,一边烧水一边喝茶,间或给娘倒上一杯,等两个暖壶都灌满了水,叔就把俩耳朵的小铁锅拎到炉子上,炒一些小的、瘪一点儿的花生米当茶肴儿。叔一早上把水喝足了,上坡干一上午的活都不停下喝一口水。
叔和娘勤扒苦做,努力地在改善家里的居住条件。第二年,叔在南墙根儿搭了一大间棚子,碰上下雨天,再不用把所有怕淋的东西都涌到堂屋里去了。又过了两年,叔在我们村西南角要了块宅基地,给大哥盖了三间玻璃门窗的瓦房,房子一收拾好,大哥和二哥就搬到新房子去住了,直到大哥结婚后,二哥还是住在大哥家的东里间。
这样,冬天的时候叔和娘也就能睡上热炕了。每天吃过晚饭,一大帮孩子就会跑到我家,围在娘的身旁听她拉呱。为了省油,我们把煤油灯吹灭,就着满院子的月光,娘把白天赶集听的评书,大概地给我们讲下来。讲完后,意犹未尽的孩子们才起身,娘赶紧把灯点上照着亮,嘱咐孩子们慢些走。我在热乎乎的炕上暖透了,赶紧穿鞋跑到堂屋,爬到床上钻进被窝一觉到天亮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, 实行村庄规划,我们整个生产队都合并到村里去了,老屋也不存在了。大家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,没有人会想念老屋,可我几回梦里,还是和姐姐通腿儿时,依偎着互相取暖;还是每晚在月光下,一大帮孩子围在娘的身边听评书;耳边还是回响着娘掐碓时,那“咯噔,咯噔”的声音……
(作者为东港区作家协会会员)